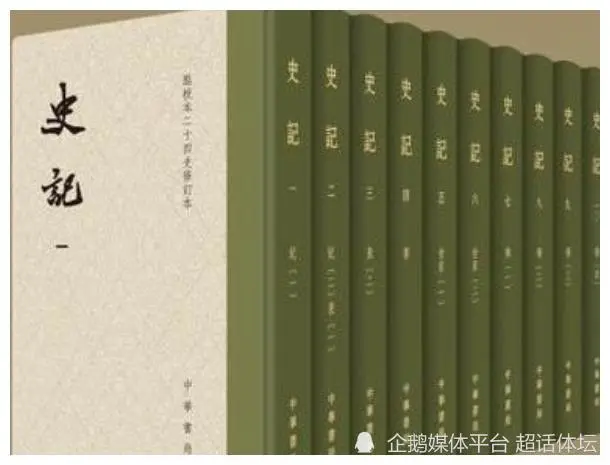江林昌:中华文明史的上古段基本上钩起来了
2023-12-05 15:01

前不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江林昌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撰文写道:过去,我们谈中华文明史一般都称“五千年”。现在,我们应该在五千年基础上加一个“多”字,完整的表述是“五千多年文明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凡谈到中华文明史,都强调五千“多”年。这个“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多”字不是随便加的,而是经历了历代学者的艰辛求证,来之不易。
江林昌(右图)曾先后师从两代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与李学勤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参加过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古文明探源工程”,任工程学术秘书。就“五千多年”这个“多”字的由来,长江日报读+专访了江林昌教授。
从司马迁、王国维到今天
几十代学人在接力
《史记》没有完成的任务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指出,他写《史记》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述往事”,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后“以思来者”。这种强烈的民族责任心成为历代中国史家共同的价值追求。
从历史学角度看,《史记》开篇为《五帝本纪》,继之以《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这些“本纪”以“世系”为坐标,以中原地区历代部族共主与君王为叙述中心,将中华文明史的上古段基本上钩稽起来了,大致包括五帝时代的文明起源与夏商周三代的早期文明发展两个阶段。
但是,这两千多年文明史尚缺年代学标尺。从年代学角度考察,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由公元前100年往上逐年推排具体的历史年代,只能排到公元前841年,即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再往上的《三代史表》,便只有世系而无具体年代了。因此,公元前841年加上公元后的2021年,总共只有2862年。也就是说,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还有前段两千多年的数据需要明确。
因此,过去在《中国通史》《辞海》《新华字典》所附录的“年表”中,有关这两段文明史的年代均不详细,这严重妨碍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全面把握。
利用甲骨文和青铜器研究年代
司马迁之后,历代学者一直在探索共和元年(前841)以前的具体年代,研究年代学的方法也一直在创新发展。
西汉刘歆在他的《三统历》《世经》中就另创天文学年代推算,即利用天象来确定年代。唐代一行的《大衍历》,宋代邵雍的《皇极经世》、刘恕的《通览前编》等,则继续“天文年代学研究”的方法,对公元前841年以前的一些年代作了进一步调整与补充。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疑古思潮,有些学者对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古史及相关年代曾经一度表示怀疑。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国维等先生从事了“古史新证”工作。1917年,王国维发表利用河南安阳新出甲骨文资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殷王世系大致可靠,其中小有差误,亦可据甲骨文而得以纠正。1925年,王国维进一步利用青铜铭文资料推断《史记·夏本纪》所载的世系亦大致可靠。王国维开创了利用地下出土文字资料来印证传世文献的古史研究新方法,为公元前841年以前的中华文明史年代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王国维基础上,甲骨学家董作宾、天文学家刘朝阳等人进一步利用甲骨文中的天文资料研究殷商王年,推进了“甲骨文年代学研究”。
刘师培、吴其昌、丁啸、陈梦家等学者根据新出土的商周青铜铭文推断商周年代,是为“青铜铭文年代学研究”。
江林昌认为,以上研究,都对文明史年代探究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体现了中国学者强烈的民族情怀与高度的学术责任心。
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大发现时代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由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与发展,学者们开始找到了一条书面文献以外的研究夏商周年代的道路。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主持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这些工作,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从而使上述传统的年代学研究能够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例如,甲骨文、青铜铭文的出土有了明确的地层关系,而相关的地层又可以取样作碳14测年。如果据甲骨文与青铜铭文推算的年月数据与碳14年代数据相吻合,那么其年代结论就大大提高了可信度。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迅猛发展,迎来了大发现时代。我们不仅发现了夏商周三代王权都城、宫殿遗址,以及相对应的诸侯方国都邑遗址,而且还有系统完整的佐证资料。司马迁《史记》所载夏商周三代的王权世系,不仅有了甲骨文、青铜铭文等出土文字资料的佐证,而且还可以落实到具体的都城遗址及其测年数据之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区系类型学”的文化历史分析,与“考古聚落形态学”的社会历史分析,更使得五帝时代的部族文化与考古学文化有了对应分析的可能。
就这样,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学术界对中华文明已获得了科学系统的认识。即在五帝时代,中华文明从各区域同时独立并起,多线发展,相互影响;到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已进入早期发展阶段,并表现为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
两大工程结出文明史硕果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与本世纪前15年,国家组织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先后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个工程首先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两个阶段作出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具体年代进行多学科论证,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具体如下:
夏代:前2070年—前1600年
商代:前1600年—前1046年
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
这是基本的年代框架。“夏商周断代工程”还对商代后期与整个西周的每位王年作了排定,如,商王武丁为前1250年—前1192年,西周武王为前1046年—前1043年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五帝时代的年代框架也作出了如下推断:
前3800年—前3300年:古国时代的初期,文明萌芽
前3300年—前2500年:古国时代的早期,文明起源
前2500年—前2000年:古国时代的晚期,文明形成
江林昌特别强调:“以上每个年代学结论的提出,都是多线索、多材料合证的结果。例如,西周王年的论证既有金文历谱的线索,又有青铜器形制、花纹演变的依据,还有地层学、科技测年的支撑;有文献学可信性的印证,更有如‘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天文推算。中华文明史的年代学是建立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的。”
公元前841年以前的文明史年代空白,现在终于补上了。中华文明史,如果从文明起源早期的前3300年算起,距今已有5300年了;如果从文明萌芽的前3800年算起,则距今已有5800年了。这就是中华文明史五千“多”年的科学依据,这是中国人民向世界的宣告。
【访谈】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重建古史
读+:中国几代学人薪火相传,终于实证了中华文明史五千“多”年,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江林昌:在中国,考古学发掘和研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重建古史,“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考古专业都设在历史系,“考古”与“文献”成了历史研究的“车之两轮”。而一大批考古学家首先都是历史学家,他们为中国古史的建立,不断推出新的成果。如,邹衡、李伯谦等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夏商周的航海史,为认识中国早期文明提供了具体资料;严文明、张忠培、俞伟超等先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为探索五帝时代文明起源作出了贡献;李学勤、裘锡圭等先生则利用一系列考古遗址、实物、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等,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建立中国古典学,提出了新的理论体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尹达、夏鼐等考古学家在全国各地考古遗址逐步增多、考古实物不断丰富的基础上,开始考虑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石兴邦、苏秉琦等人逐步创立中国考古区系类型学,赵辉、栾丰实、王巍等新一代考古学家又继续发展了考古聚落形态学。
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家相继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逐步建立起了公元前841年以前所空缺的中华文明史的前两千多年的年代学标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终于有了实物支撑和科学论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为中华文明史建立年代学标尺意义重大
读+:为中华文明史建立年代学标尺,有什么意义?
江林昌:在世界原生态古文明中,西亚两河流域最早的乌鲁克文明与北非尼罗河流域最早的涅伽达文明,都起源于距今5500年左右。而且,在几代西方学者的努力下,西亚两河流域古文明从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先后发展的古文明都有了完整的年表,埃及古文明从前王朝—早期王朝—古王朝—中王朝—新王朝等相继发展的古文明也有了完整的年表。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史完整年表则是最近二三十年才逐步建立的。
1995年下半年,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了在京的部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和科技测年专家进行座谈。学者们表示,建立夏商周年代学,是相关学科专家们的共同愿望。此后,宋健同志又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共同多次主持会议,广泛征求了专家们的意见,并联络相关的部委,共同酝酿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筹备,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和宋健再次在国务院主持会议,代表国务院宣布启动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旨在通过政府的支持,依靠专家的联合攻关,使千百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夏商周年代学问题,进一步科学化和量化,最终为探索中华古文明的起源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根据项目成果: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前,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5000年前,我国出现了国家,进入“古国时代”。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科学论证、庄严宣告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意义是深远的。从学术史角度讲,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论证,表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让世人信服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华文明的内涵特色,总结中华文明的一系列规律,建构中华文明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中国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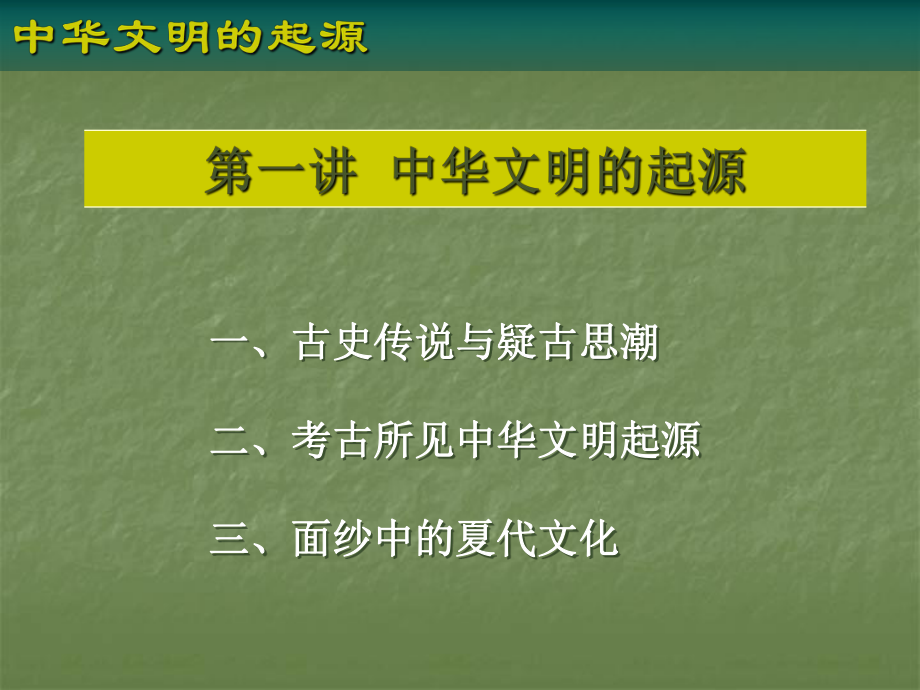
有一分证据、有一分材料,就说一分话
读+:您先后参与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大家是否有意识地想把中华文明史往前推呢?
江林昌:完全没有!我可以告诉你,在学术上,参加这两个工程的科学家都是非常严谨,有一分证据、有一分材料,就说一分话。当时我是学术秘书,有时候我通知大家第二天开会了,大家就会预测:你看着吧,明天谁谁肯定要和谁谁争起来。第二天,他们在会上果然争得面红耳赤,非常激烈。但是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家又和和气气了,因为都是为了学术而争、为科学而争。
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参加工程的时候,完全没有预见到会把中华文明史推进到五千多年前,当时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能证明五千年文明,那就很了不得了。可是,我们的考古重大发现一个接一个,我们的科技手段日新月异,我们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考古成果。是这些材料、这些成果把我们的结论一步步往前推,让我们不断更新对中华文明史的认识。
举例来说,原来我们有中原文明一元论;后来苏秉琦先生依据“六大文化起源区”,提出了“满天星斗说”,这就打破了中原文明一元论;再后来,我们发现文化起源区不止六个,还有巴蜀区,也就是三星堆文化,还有关中区,也就是石峁文化。这是任何文献上都没有记载过的,所以我们的认识再一次被实践所推进,现在是八大文化起源区。
再比如良渚文化,上世纪30年代就在当地发现了玉器,80年代发现了祭坛夏商周的航海史,到本世纪发现了水坝系统。每一次发现,都改写了我们对良渚的认知,现在公认,良渚文化应该称为良渚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国家级水平。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老师李学勤先生一件往事。当年,他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期间,撰写了大量学术文章,涉及天文学、甲骨学、考古学、文献学等多个学科,这些文章编撰成书的时候,他特别要求,不要按照学科来分类,要按照文章讨论的年代来分。这样一来,我就发现,在围绕同一个年代主题的讨论中,往往出现“自我否定”的情况,甚至有“否定之否定”,看得很清楚。我问李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他回答:这样才能看出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发展过程。那为什么要把自己被否定的文章放进去,不怕丢面子吗?这就是学术史!让后人看看,我们是怎样在未知中探索、逐步走向真理的。
那时我还很年轻,李先生这种敢于求真的精神,影响了我一辈子。
要读懂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规律
读+:“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后,中华文明史是否还有空白需要填补?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江林昌:这两个工程取得的成果是框架性的,在框架之中,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研究,比如夏代。同时,现有的结论只能说明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界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但不是最后的结论。如果将来出现考古新材料而推翻工程的某些现有结论,那也是正常的。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从社会政治角度看,世界上几个原生态古文明中,中华文明同样具有起源的早期性;而且,中华文明是几个原生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绵延至今的。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在新时代,中国古史研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作出新的贡献。
其一,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全面总结马恩经典著作中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建立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马恩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经历了一百多年时间。我们应该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深入钻研马恩经典著作,梳理出其中的相关论断,然后根据有关新旧史料,对中国古代社会作出合理分析。例如奴隶制问题。
其二,努力构建中国古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具体过程,揭示中华文明的内涵特征。中国古代文明在起源发展阶段,表现出很多与西方文明不一样的特征,因而其内涵也有诸多不同。中国古代独特和优越的地理气候环境,促成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形成。这与古希腊、小亚细亚的航海商贸文明,欧亚大陆北部的游牧文明形成了鲜明不同。农耕生产需要聚族定居,因此中国先民很早就有祖先崇拜、强调血缘族团,形成了“家国一体”的观念。中国的农耕生产与血缘管理,使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归纳总结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规律,不仅有利于构建中国古代文明理论体系,而且这个体系还有环太平洋古代诸文明的代表性。这个代表性的意义在于它体现出世界古文明的中国特殊性,对于人们深刻认识历史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