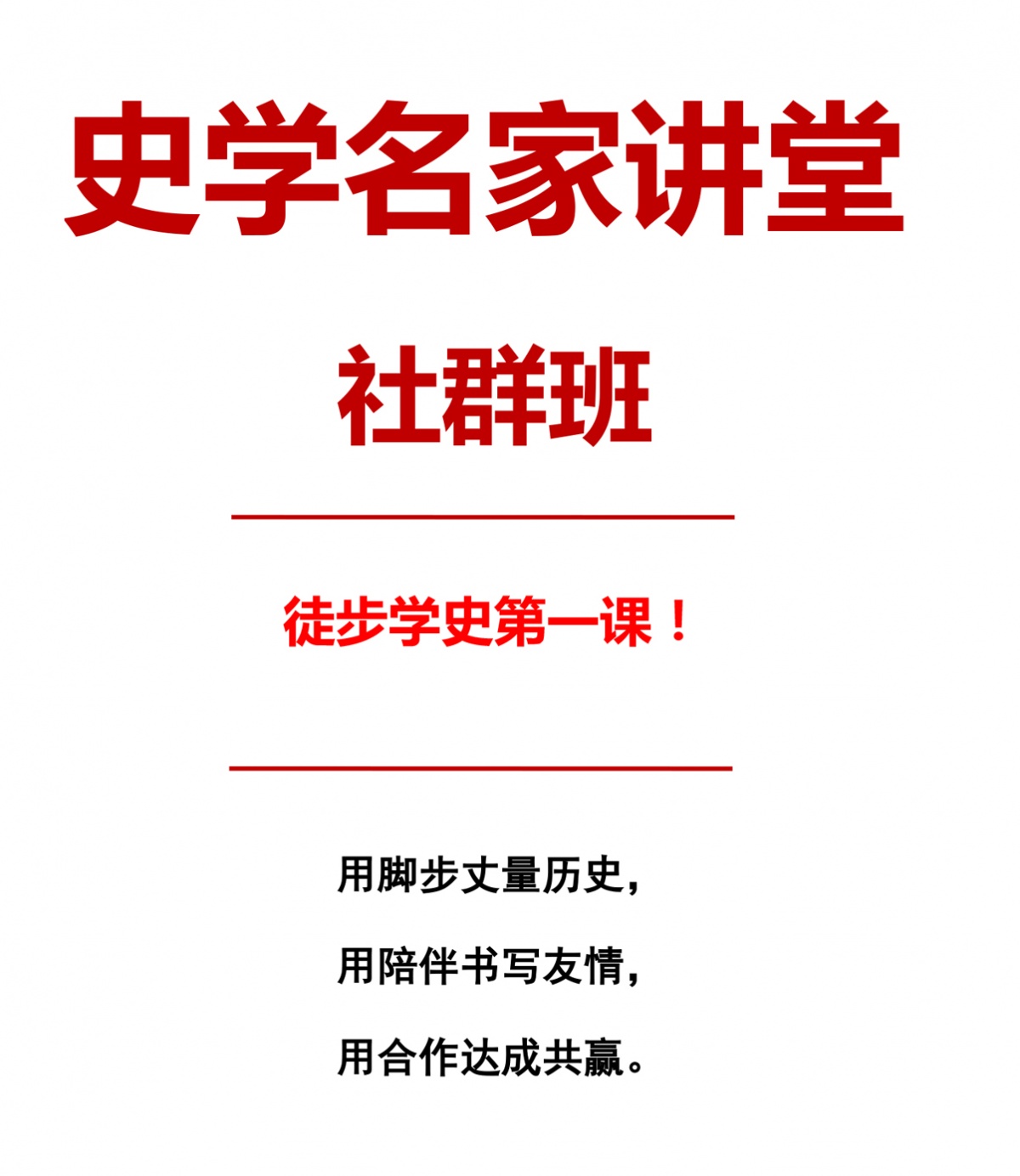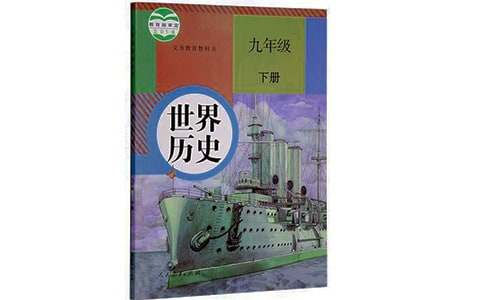:“通史家风”的主旨是什么?
2023-05-31 14:02
讨论“通史家风”,离不开对“断代为史”的认识,这不仅是因为“通史”和“断代”是传统历史编纂的两种基本格局,是古代史家“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而且是因为“通史”和“断代”在著史宗旨和思想观念方面既有对立和矛盾,又有统一和包容,涉及中国传统史学诸多本质性问题,理应深入探讨。
一、“通史家风”的主旨
毋庸置疑,中国史学有重“通”的传统。揆诸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从西汉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并撰成纪传体通史《史记》到清代章学诚提出“通史家风”并以此衡评前代史著,人们对以“通”为史的阐释一直没有间断,“通史家风”的理论内涵不断被丰富。可是,“通史家风”的主旨是什么呢?换言之,何为“通史家风”之核心内涵?对此,当代学者的认识颇不一致。许凌云认为“通史风”的主旨体现在三个方面:“成一家之言的著书之旨”;“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的作史规模”;“通古今之变的作史方法”。吴海兰认为“通史家风”既表现为“通古今之变”的纵通,又表现为“会天下之书于一手”的横通,纵横交织,构成了“通史家风”的整体性特征。这些认识,如果就通史而论通史,都能站住脚,但如果与“断代为史”放在一起讨论,很多结论都是值得商榷的。
要想弄清“通史家风”的主旨,必须回到古代史学发展的实际和古代史家对“通史”的理论认识中去。古代史家讨论“通史”,以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章学诚等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归纳他们的论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谓“通史家风”,从最初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纵通”,到郑樵的“会通”,再到章学诚讨论通史时提出的“横通”,其内容有一个不断被叠加的过程。 如果我们只从“通史”的角度审视这些内容,可能会把它们都当作“通史家风”的内涵而加以接受,但如果从“断代史”的角度审视这些内容国史通鉴春秋战国篇有声,就会发现这种叠加不是丰富了“通史家风”的内涵,而是冲淡或模糊了“通史家风”的主旨。
“纵通”,即贯通古今,追源溯流,把历史当作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呈现历史自始至终的演变和联系。 此当以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最具代表性,杜佑、司马光亦是这一理论的追随者。司马迁著《史记》,上起黄帝,下终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古代通史之作的发端。杜佑撰《通典》,上起黄帝,下迄唐天宝之末,是典制体通史的代表作。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同样是通史编纂的典范。这些著作,“纵通”的特点非常鲜明,即“原始察终”“通古今之变”。
“会通”是南宋郑樵极力提倡的作史方法,其“会通”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献资料的“会”,“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二是古今历史的“通”,“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国史通鉴春秋战国篇有声,然后能极古今之变”。 与郑樵类似,马端临的“会通”观也是两个方面,一是纵向上考察典制的“会通因仍之道”和“变通弛张之故”;二是横向上考文征献,广搜四部资料,遍录群儒议论 。显然,郑樵、马端临在“通古今之变”基础上增加了文献上的“会通”,即融会贯穿各类史料以著史。章学诚讨论通史,提到“横通”。章氏的“横通”,有批评学界炫耀知识渊博之意,但同时他又认为对于“纵通”而言,“横通”的价值不可忽视,因为可“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之纵”。
“横通”是完成“纵通”的必备条件。如此看来,其“横通”也就有了渊博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著述内容之含义。 其实,旱在章学诚之前,王夫之曾对《资治通鉴》之“通”有一番解释,“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这实际上是从“横通”的角度解释了《通鉴》所涉及到的社会历史内容,指出《通鉴》就是在融会贯通了这些内容后而自成一家之言的。很显然,“横通”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史著所载社会历史内容的考量。
正是因为古代史家在“通古今之变”基础上不断叠加新内容,所以导致当代史家在认识“通史家风”时,往往把这些内容都当作“通史家风”的内涵。其实,当我们以“断代为史”为参照,审视“纵通”“会通”和“横通”,就会发现,文献资料上的“会通”和历史内容上的“横通”都不足以反映“通史家风”的主旨。这是因为“会通”和“横通”,断代史家也完全可以做到。在中国史学史上,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只要是优秀的史著,都需要广泛占有文献资料以及反映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这样才能留传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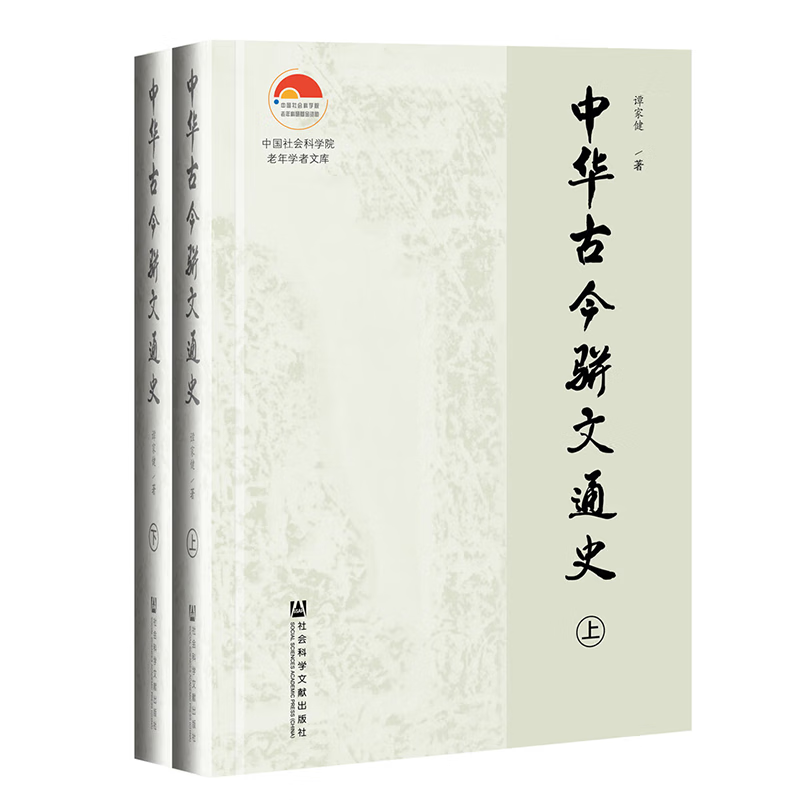
司马迁作《史记》,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反映几千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风土人情、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班固撰《汉书》,同样要“探纂前记,缀辑所闻”,彰显西汉一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风土人情、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坚持通史的郑樵强调“会天下之书于一手”,肯定断代的刘知幾同样强调“征求异说,采摭群言”。“会通”文献资料和“横通”历史内容,是古代所有史家都必须具备的修养,所谓“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可见,文献资料的“会通”和历史内容的“横通”是作史的基础性工作,并非通史所独有之思想特色,故而不是“通史家风”的主旨。“通史家风”的主旨只能是“通古今之变”,“不通古今之变,则无以言通史”。“‘通古今之变’就是通史的精神”。可见,“通史家风”是围绕“通古今之变”而形成的别具一格的理论体系。
其一,“通古今之变”是“通史家风”的思想核心,强调的是以整体联系的“通识”眼光看待社会历史的变化,探求社会历史的事理法则。 围绕“通古今之变”这一主题,古代史家提出了古今、始终、往来、盛衰、损益、变通、理乱、得失等一系列概念,形成了系统的有关通史的理论认识。“只有意识到要把过去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去看待的时候,才能产生通史的观念,也就是说通史必须意识到,要把对一个朝代的总结扩展到对整个历史的总结”。司马迁作《史记》,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终始古今,深观时变”,“述往事,思来者”,“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杜佑作《通典》,“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酌古之要,适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斟酌理乱,详览古今”。司马光认为“治乱之原,古今同体”,“治乱之道,古今一贯”。其作《通鉴》,乃“监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他们都自觉地把“承敝通变”与“贯通古今”联系起来考察,将历史看作是一个连续的整体,用联系的眼光考察古今变化,在古今变化中思索治乱安危存亡之道。 “通史的意境,全在通古今之变,历史由此才重现出它的节律脉动,是一个活泼泼的跳动着的‘集体生命体’,有它特殊的生命历程和内在的新陈代谢机制” 。
其二,“别识心裁”是“通史家风”的理论特色,强调的是撰述历史必须要有“成一家之言”的胆魄,要有对历史发展的独特见解。 司马迁著《史记》,倡导“成一家之言”,杜佑著《通典》,“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李瀚:《序》,杜佑:《通典》),郑樵撰《通志》,被誉为“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可见,“别识心裁”“成一家言”本身就是“通史家风”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中国史学史上,章学诚论“通史家风”,特别重视“别识心裁”,认为通史撰述绝不是没有宗旨的无所不通。在他看来,体例上的“时历古今”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思想层面的“成一家之言”。他认为,并非贯穿上下的史书都有资格称之为“通史”,譬如李延寿的《南史》《北史》、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罗泌的《路史》等,表面看贯通数代,“体与通史相仿”,但实际上有天壤之别,不能叫做通史,只能叫做“集史”。因为通史“源自古初,及乎作者之世,别出心裁,成其家学”,而集史只是“合数代而称为一书”,并无别识心裁,与通史貌合神离。有鉴于此,章学诚指出:“凡所谓通史者,不问纪载短长,学问疏密,要有卓然独见,迥出前人。”通史之作,叙事自古及今,所叙述的历史过程基本相同,如果没有“自成一家”的撰述宗旨,没有独具匠心的“别识心裁”,必然会重复前人,从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可见,“别识心裁”“成一家言”是认识“通史家风”的重要锁钥。
二、王朝正统与“通古今”
对于“通史”和“断代”孰优孰劣,古人衡长较短,仁智互见。刘知幾推崇断代,批评通史。他高度评价班固撰《汉书》,“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工。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强烈批评司马迁作《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每论国家一致,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和刘知幾不同,郑樵、马端临推崇通史,批评断代。他们认为通史之作,能“同天下之文”,“极古今之变”,而断代为书,“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会通之道,自此失矣”,“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章学诚则站在“史意”的高度,深入阐述了“通史家风”的意旨,充分肯定了通史撰述的价值,并指出“易通史为断代,宗旨已不侔矣”。可以说,无论是刘知幾从“史法”角度对通史进行批评,还是郑樵等人从“史意”角度对断代进行否定,其思维方式都是把通史和断代对立起来,鲜少注意二者之间有相通之处。
及至当代,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一些学者开始挖掘断代史中所蕴含的“通古今”观念,如刘家和先生认为《汉书》虽然在体例上是断代史,但其中的八表、十志却能够上下贯通,充满了通史精神,并认为“《汉书》以下各正史,尽管著述水平参差不齐,但大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吴风霞则指出元代修宋、辽、金三史,虽断代为史,但其中的一些论赞却运用了“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方法,并断言“《汉书》以下各断代史,都不同程度地遵循了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方法,贯彻了通史的精神”。

古人和今人对古代史家历史书写中“通”与“断”的不同思考,涉及到我们对“通史家风”深层问题的认识,促使我们不得不对以下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断代为史的宗旨究竟是什么?断代史中有没有“通古今”的观念?如果有,其与通史中的“通古今之变”的观念是否相同?其目的又是什么?看来有必要辨析一番。
中国古代优秀的断代史著中确乎有着“通古今”的观念。班固撰《汉书》,曾自述“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函雅故,通古今”。荀悦著《汉纪》,要“达道义”“章法式’川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袁宏作《后汉纪》,也申明“通古今而笃名教”。如此等等,都在“断代为史”时提到“通古今”。那么,断代为史何以要“通古今”呢?其答案就是:要在古今对比中树立王朝正统,凸显王朝历史地位。
把“通古今”的观念寓于断代史著之中,以树立王朝正统,凸显王朝历史地位,始于班固撰《汉书》。 班固对司马迁撰通史,把西汉“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非常不满,认为这不利于宣扬“汉德”,无法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他曾批评同时代的学者只会咏诵讲论《诗》《书》《礼》《易》《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 为了达到“究汉德之所由”这一目的,他抛开了司马迁基于真实历史过程的“通古今之变”的做法,另搞一套神意的(天意的)“通古今”,重新树立汉王朝的正统 。他著《典引》,把汉朝历史追溯到唐尧,构建出一套刘氏政权的神授(天授)体系,所谓“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踪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禅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公元首,将授刘汉”。汉朝本承秦、项而立,和之前的王朝没有什么不同,但经过班固这一番“上下洽通”的操作,汉王朝竟然上接帝尧统续,“冠德于百王”,历史地位陡然得以提高。为了树立汉朝的正统地位,班固反复申说“汉绍尧运”,诸如“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皇矣汉祖,纂尧之续”等。通过这样的包装,刘氏即帝位,“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列精,蕴孔佐之弘陈”。很显然,班固认为汉朝的正统得自上天所赐,乃尧运所归,得孔子所助。可以说,《汉书》断汉为史,包举一代,就是要通过这种神意的“通古今”的考察,宣扬汉德,匡正汉主,树立汉朝正统,凸显汉朝历史地位,这是班固撰作《汉书》的第一宗旨。文廷式曾言:“班孟坚作《汉书》,断代为史,故前不纪项籍,后不纪王莽,所以尊本朝,与史迁作通史之例异。”可谓一针见血。
与班固类似,荀悦于《汉纪》中“通古今”,也是要在古今对比中彰显汉朝威德,“昔在上圣,惟建皇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乃作书契,以通宇宙,扬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厥后,永世作典……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袁宏在《后汉纪》中“通古今”,目的是为了“笃名教”,治心化民,“弘敷王道”,“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由此可见,断代为史而标榜“通古今”,其宗旨和目的就是彰显“继统”“述德”的理念,为王朝争正统,以说明王朝建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自班固断汉为史以反映王朝历史以来,“弥纶一代”“网罗一代”“包举一代”“勒成一代”的“一家之史”和“一朝之史”极为盛行,以“继统”“述德”为核心的作史理念,完全被后世断代史家和统治者所继承,通过神意的“通古今”来论说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分裂割据政权“缀述国史”,要么为了“推奉正朔”,要么为了“假名窃号”,以表示各自政权的正统地位。大一统政权修史,则强调“盛业宏勋,咸使详备”,同样是强化王朝正统。《汉书》以下正史皆为断代史,这些“一家一姓”的史书虽然反映不同王朝的历史,或“续统述德”,或“以史治心”,或“专事褒贬”,或“力辨正统”,但实际上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编纂旨意,那就是强调各自政权的正统地位和合法性,而以别人为偏霸,遮蔽不符合王朝利益的记载。因此,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作为断代史标志的历朝正史,代表王朝的利益,依靠政治的力量,打着“通古今”的幌子,以得天之正统的神意史观解释王朝建立的合理,其宗旨与“通古今之变”截然不同。
今人讨论“断代为史”中的“通古今”,往往认为断代史在典章制度的记述上能够上下贯通,具有“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精神,实际上这种认识也是偏颇的。毋庸讳言,典章制度有因革损益,如果不能探本求源,必定造成“原委不明”。 但我们必须看到,断代史叙述典制源流,其落脚点是在本朝,是为了说明本朝制度的完善,这和通史叙述典制源流力主“会通因仍之道”,推寻“变通驰张之故”有极大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譬如《汉书》十志,确乎有“扬榷古今”“正其终始”的特点,但与《史记》八书的编纂思想比较,就能看出价值取向的差异。《汉书·叙传》阐述“十志”撰述宗旨,关注点在汉王朝,诸如“汉章九法,太宗改作,轻重之差,世有定籍”,“降及秦汉,革划五等,制立郡县”,“爰及沟渠,利我国家”,“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等,价值指向在于通过“扬榷古今”而“宣汉”和彰显“汉德”。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阐述“八书”撰述宗旨,没有一处言及汉朝,而是打通古今考量典制沿革,关注点在“略协古今之变”,“切近世,极人变”,价值指向在于通过“通古今之变”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可见,“断代为史”中的“通古今”观念与“通史家风”中的“通古今之变”观念在宗旨和目的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断代为史”意在凸显王朝正统,其“通古今”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考察历史盛衰、探求历史因变,而是要把王朝的历史放到古今变化中,以一种脱离历史实际的神意的方式建构其不可替代之地位,说明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也就不难理解,自班固断汉为史以后,纪传体断代史之作尽管“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呆板僵化,但依然兴旺发达,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较好地满足了专制王朝的需要。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班固,还是荀悦、袁宏,都说自己“通古今”,没说“通古今之变”,这大概也是和他们撰述断代史是为了树立王朝正统而非探求古今盛衰变化的目的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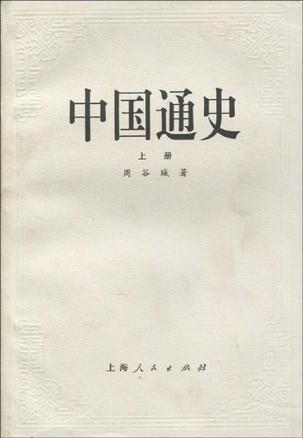
三、“通”与“断”:两种不同的史学旨趣
古人讨论“通史”和“断代”,或尊“通”而抑“断”,或尊“断”而抑“通”,此疆彼界,争论不休,多数还都停留在“史法”层面上。实际上,“通史”和“断代”不仅是史书体例和断限的区别,更是著史宗旨的区别,是“史义”和“旨趣”的区别。
“通史家风”与“断代为史”的落脚点都是现实社会,但它们关注的问题却有极大的不同,对历史的理解及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存在重大差异。二者奇妙地共存于专制社会的史学体系之中,体现了传统史学的诸多本质特征。
“通史”强调撰述和认识历史,应该把历史当作一个因革变通的不断延续的过程,既推原其始,又察究其终,在历史的长时段里总结历史盛衰,探寻“成败兴坏之理”。 “通史家风”有着相对理性的历史眼光,能超越个别的、局部的现象,把古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藏往知来”,“疏通知远”,认识到每个王朝和个人在历史上都有其位置,但功过是非必须放在历史长河中才能看清楚。“通古今之变”并非空泛总结历史规律,其“述往事,思来者”,有着实际的历史内容,“既要条理制度的文野进退,这是‘明变始终’的大关节;也不废有关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人事兴替,以期明乎‘造变’多因,目的是为人类‘知来’指名道路”。“通史”落脚于现实,无非是要告诉统治者,治国安邦,必须寻求某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政随时移,制随俗变,顺应时代潮流而变通。
“断代”则更多地强调历史撰述的政治功能,多是基于政治需要而考察历史,树立正统,以服务现实,有着强烈的政治性与功利性。断代为史,尊一朝正统,“正一代得失”,总结一朝之历史经验,抱持着一种明显的政治目的,旨在论证王朝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在中国古代,正史是“断代为史”的标志性成果,自唐代设馆修史,正史修纂一直被统治者把控,历史的解释权完全被统治者垄断,包举一代的王朝史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有选择地建构起“一家之史”,为专制制度张目。断代王朝史沦为统治者彰显自我地位的工具,成了史学屈从于政治的标志物,其旨趣自然与“通史”有别。
吴怀祺先生曾提出,在专制统治者二重性的要求下,中国传统史学具有二重性,即一方面尊重历史真实,直书实录,一方面则虚构历史,以为统治者所用。实际上,通史和断代史也适应了专制帝王对史学的二重性要求,一方面,通史“通古今之变”,满足了统治者吸取真实的历史经验的要求,断代史“考一代得失”,虚构皇权神授和王朝正统,满足了统治者意欲证明自身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要求。从历史上看,统治者对抽象的规律性的经验总结也不一概排斥,但他们更需要直接说明自身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探寻历史的古今之变和按照统治者的要求歪曲、虚构历史,二者奇妙地统一于传统史学之中。
总之,“通史家风”和“断代为史”是中国史学的两大传统。从其总体特征看,“通史家风”意在考察历史盛衰之变,彰显人类认识与把握历史规律的能力,故多为史家所赞赏;“断代为史”意在树立王朝正统,彰显王朝历史地位,故多为统治者所提倡。如果说“通史”因要“通古今之变”,对历史尚具有某种反省及反思的趋向的话,那么“断代”就几乎完全陷于以王朝为中心的泥潭之中了。
作者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注释从略。
推荐阅读:
下一篇: (知识点)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春秋战国